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我在山口,背朝已到了山的另一侧的影子,乌云奔流,夕阳赶忙弯折,慌乱刺伤了我仍望着你的神经。而我已烧毁、融化,待云雾夹杂的雨一滴一滴袭来,又把我浇筑成人的模样。
我在荒原,东北方是起重机与繁茂生长的水泥,于是趁着雨,吞食山石、山木、山雾,山的一切,成为电梯,快速来到了,比雨还要高的明星。我只看到云雨不断灭亡,又再度新生,如同神明。
我是群山,无法再度移动我的脚步向更东北方迁徙,在四面撒上钢铁荆棘的种子,埋葬着同为山的尸体。我成为时代,便举头发问为何出口是繁星,繁星是云雾?为何云只一片一片地来,又无声无息离去?为何我在发问,仍在等待回音?
我便想见到你。想逃出所谓的雾,逃出这个山口,我无从分辨山与人群,或是我的躯体想逃出这场雨,逃向她所途径的天空,我无从分割人与抽离,我便见到鸟群,我成为群山,成为鸟雀,成为迷魂,逃向孤身的漫游、困惑、不解。逃出时代。
就着雨,我咽下一张纸裁的月亮,它们我的肺腔唱着歌,不知被消化成了什么。我也只望着这雨,缓缓向东北方的山口踱步,如往常一样。彗星带着雨,一片飘走,也只等着下一片。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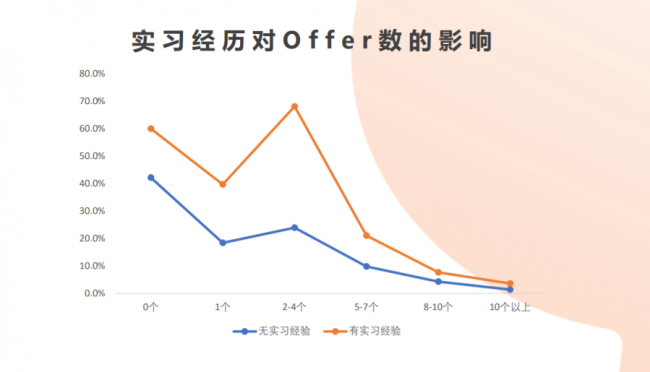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
营业执照公示信息